《独眼利霍》:开场就揭底牌,宿命实现的过程成为最大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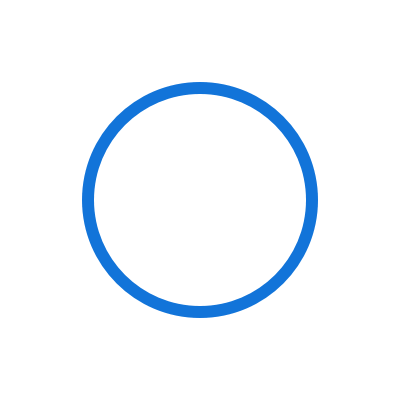
- # 电子游戏
- # steam游戏
- # 独立游戏
- # 玩家杂谈
- # 营地测评
本文为作者原创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和营地同意不得转载

《独眼利霍》,由俄罗斯独立团队Morteshka开发并发行,一款基于斯拉夫文化所进行创作的步行模拟器恐怖冒险游戏。带有一些比较中规中矩的解谜元素,解谜形式不多,没有太多令人惊艳的部分。游戏的游玩时长大约在5个小时左右,可玩深度上并没有太多维度,提示适中,而且只有前半部分带点恐怖色彩。
传说中,利霍(Likho)是邪恶命运与不幸的化身,一具独眼的瘦骨老太婆,象征着人无法摆脱的厄运轮回。玩家在游戏中,成为了这类民俗故事的主人公。该游戏称得上近年来东欧独立游戏中的佳作之一,比较适合想体验文化寓言,具备耐心探索气氛与意象深意的玩家。

叙事能力与画面表现的出色是该游戏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它对于这条线的叙事十分出色,但是它只有这一条线。也就是说,它没有重复游玩的价值,它仅提供这一次性的游戏体验。
游戏没有任何色彩,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不带感情地阐述着这则改编自民俗的故事,大多数玩家对这些文化并不熟悉,因此那种陌生感就带来了一层神秘。而黑白画面本身带有比较沉重的感情基调,配合上大众相较陌生的文化,时不时陷入黑暗的压力塑造。这就是这款游戏塑造心理恐怖的方式,视觉上的冷漠,和文化上的远。


主角是一名铁匠,像其他传说中的英雄一样,感受到了某种模糊力量的征召。一开始他在敲击铁砧的节奏里,落锤瞬间,画面变成一只吞噬月亮的乌鸦,接着杯子放下,在醉意模糊的视野中,对桌依稀可辨一个诡异的人形。像是梦境,也像是幻觉,又或者是为了表现出现实的折叠。通过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加上不同画幅的连贯视觉表现,那些看似毫无逻辑的意象被逐个串联起来,或许从第一记落锤开始,游戏就将玩家丢入了兔子洞。
裁缝说,我们的故事一定不寡淡,游戏包含着众多民间传说中同样的内核;裁缝还说,他想要织出一件绝无仅有的卡夫坦,可惜主角并不是伊阿宋,而是一名平庸的铁匠。


夜里,铁匠开始踏上属于他的路途,一如那些传说的开头,裁缝站在村口说,带上我吧,铁匠答应了。于是,两个没有姓名的人一同走进漆黑,又繁星满布的森林小路。他们一边前行,一边用俄语低声自述着故事和人生的虚无。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是如何找到的方向,他们只想见到利霍,他们想见一点真东西。

游戏中一路上存在着一些收集元素,散落各处的白桦树皮信,里面有时候是散文有时候是诗歌。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信中的内容用一种故事节选的感觉描述了主角当前的境遇,有时候又是在预示着前方的挑战与困难。除了白桦树皮信以外,游戏中额外的解谜环节还能解锁名为世界之书的章节内容,这些章节全部来自于以斯拉夫文化为主的真实民间传说,他们之间共同的主题是独眼巨人的试炼、命运丝线以及不可避免的牺牲。这部分内容多到几乎是一个主题性的百科全书。如果有人喜欢小故事,那一定会在这部分得到乐趣。我很喜欢一则Steam评测中所用的词,皮薄肉多,对于喜爱民间传说的玩家而言,确实如此。玩家既在读古往今来的故事,一边也活在故事正发生的此刻。


有时,场景会陷入一整片黑暗,好在玩家手里有一盒永远划不完的火柴。这点小小的火种,在游戏里发挥出了非常多的作用,除开解谜的用途以外,某些情况下玩家甚至能够出于发泄来烧掉一切可以燃烧的物品。考虑到游戏的性质,每次点燃火柴,我总会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火柴,看到眼前那一点点温暖和光明,然后火焰熄灭,黑暗又重新笼罩。何况有时候一划火柴场景就会发生变化,正如小女孩划燃火柴后看到的幻象一样难辨虚实。




由于某种超自然力量,或者游戏中所说的某种邪恶的力量,穿过森立后的玩家从一座林中小屋开始,一直到结尾,几乎能够遍历世界之书中的情节。树皮信上所说的一切,试炼、困境、相遇与别离,都一一应验。这款游戏在一开始便向玩家剧透游戏所有的重要情节,既然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为什么我们还愿意走下去?
即使玩家对斯拉夫传说略知一二,即便游戏时时刻刻地从那些故事中进行剧透,《独眼利霍》依然有趣。这种现象恰巧体现出游戏的叙事与传统线性叙事的区别之一,即玩家可以切身参与和体验故事的过程,介入其中,然后经历,感受,而不只是接受讲述。游戏不断通过故事与传说预知剧情的叙事方式,反而增强了一种悬置的宿命感和戏剧张力。每一则故事中,相似场景会重现,抉择也一再出现,但玩家导致的细节与视角变化让我们得以窥见故事新的侧面。
我知道自己正在重演寓言,也知道终点,却仍然忍不住一步步走下去。玩家和那个像维吉尔一样引路的裁缝,在利霍的世界中漫步,经历试炼,穿行在阴影下。那些充当预言的故事与诗歌散文,变成了镌刻在石板上不可撼动的命运象征。那些模糊的预言,在体验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拥有实体的现实。


如果结局不能改变,那过程还有意义吗?或许这就是这款游戏想表达的之一,对于意义的理解有时候不止是故事“讲了什么”,同样在于故事“如何”被讲述。叙事的方式本身就能成为意义,所以哪怕我们知道结局会去向何方,但依然令人好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过程,本身就是故事意义的一部分。

当铁匠点燃熄灭的火柴,再次照亮脚下的路时,我们清楚黑暗中会发生什么,却依然会因为火光的消逝而心头一紧。当裁缝在门后呼喊,我们知道他难逃厄运,却还是会加快脚步替他开门。我们知道宿命不会改变,但依旧想在一次次重复里找到转机,为此抱有侥幸。这种想要改写的冲动很多时候不是理性判断,更近似于一种直觉的本能。就像《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2006)里,松子准备了结自己的生命,却在最后一刻本能地抓住栏杆。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题材中,先知之所以痛苦,他们明知未来,却总忍不住期待,也许还能改变些什么。
另一方面,游戏还提供一种选择上的幻觉。表面上,我们似乎在多个节点上拥有决定剧情走向的权力,但最终无论怎么选,还是逃不开既定的命运。这种体验很微妙,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掌控一切,越走越远后却发现, 一切仍然在滑向并朝着原来的结局坠落。最后接受所有道路殊途同归的残酷,越是奋力抗争,悲剧来临时的无力感越强。


“有可能一个故事是一个寓意,也有可能所有故事都是一回事。”裁缝这么说过。他又自问自答,一个故事究竟由谁决定?说不定是谁经历过,然后将自己的事迹传出去,而时间一久,这些亲身经历也就成了民间故事。而这款游戏,通过剧透与逐渐落实的过程,来让玩家亲自去实现那些传闻中的故事。在终点,故事讲完,玩家也悄悄成了下一个传说的一部分。
有人形容,这个游戏的整体视觉像是一部1909年的俄国默片,胶片噪点、硬质对比。除开频繁出现的碎片化意象,黑白色调让视觉语言本身变得更直接。没有色彩的干扰,线条,轮廓,光影……都更清晰地跳出来,尤其是在那些几乎全黑的场景中,远比彩色画面更容易让人感到孤独、无助,也更孤立无援。


很多场景的构图和镜头调度,能看见许多电影以及戏剧质感的表现。星空与云层在某个瞬间凝结成一只巨大的眼睛悬于天际,裁缝惊呼:“看哪,主的眼目!”。逐渐坠落的坟墓,眩晕感和无路可逃的绝望一起向下拖拽。在祭坛上操纵月亮阴晴圆缺的瞬间,也从侧面意味着神祇视角的创造与毁灭性力量。在追击的间隙中,割下羊毛,而那只绵羊却转过头唱起了童谣。这些画面没有直接的解释,却能在这种荒诞中感受到暗示。
划亮火柴时那一声清脆的嘶响和跃动的火光,永远新鲜。火苗烧尽,熄灭,短暂地陷入黑暗,再度慎重地点燃下一根。节奏周而复始,某种挣扎与仪式感也油然而生,这个世界里,好像只有火光照亮的地方才让人感到安全,或者说,是唯一还算真实的地方。
《独眼利霍》带来的体验或许晦涩而怪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念,窥探黑暗真相的好奇,以及在命运面前自作聪明的荒谬。到最后只剩下黑暗,一只眼睛从中凝视,冰冷,漠然。点燃火柴,微弱的光映出墙上一行潦草的涂鸦:“Мы все переродимся”(我们都将重生)。
总体评分
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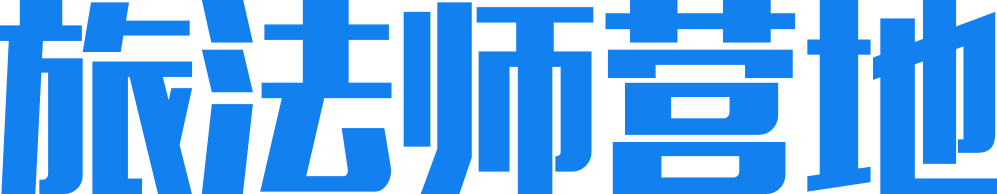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