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伪人》:恐怖与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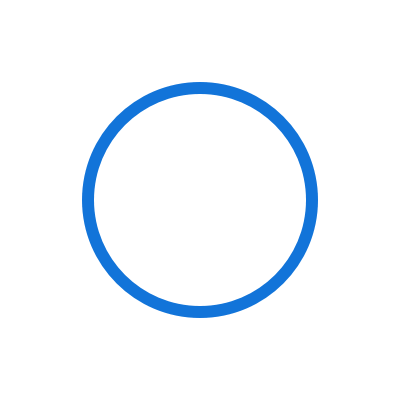
- # 电子游戏
- # steam游戏
- # 营地测评
- # 玩家杂谈
本文为作者原创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和营地同意不得转载
笔者:日月空天
2025年9月23日
本篇约4000字,推荐阅读时间15分钟。
《寻找伪人》(No, I'm not a Human)已于9月16日上线Steam. 此前,其早期测试版本曾在视频平台引发超千万级别的关注量。非常有幸,笔者受营地之邀来游玩体验并作一篇测评,也想要在此与诸位分享一些我对泛恐怖题材与价值信念的思考。
(本篇无剧透)

近年来,"伪人"类游戏作为一种新型的恐怖游戏亚类型在玩家社群中悄然兴起。它摒弃了传统的血腥暴力和突发惊吓(Jump Scare),转而专注于一种更深邃、更持久的心理不安。这一类型的核心对象是“伪人”——模仿人类形态的未知实体,而其常见的表现形式则是一种唤起怀旧感与技术疏离感的美学风格。本章节将对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拆解,并探讨它们如何协同作用,构建出一种全新的互动式恐惧体验。
- 社会信任度下降、对“他者”的猜疑
- 熟悉的世界变得不同、失序
- 不可靠的媒介、不可靠的人
- 本应安全、美好的世界(未受干预的、带有滤镜的旧世界)下的威胁
由表象到内在
近年来,“伪人”类游戏层出不穷,笔者认为其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I'm on Observation Duty》。虽然这款游戏并不包含“伪人”:游戏内容仅仅是寻找监控视角下空间的“异常”,但其内核与如今的“伪人”游戏:熟悉环境/对象的异常,复古的美学风格与落后的技术媒介等是高度一致,能够看出其顺承的关系。
如果说《I'm on Observation Duty》引领起了“异常”游戏、“伪人”恐怖的第一波浪潮,那么《寻找伪人》则很有可能代表了该类型的演进方向。这款游戏在正式发售前,仅凭一个试玩版就在玩家社群中积累了极高的期待值,甚至吸引了许多通常不玩恐怖游戏的玩家。与前者的纯粹机制驱动不同,《寻找伪人》更侧重于叙事、对话和复杂的道德抉择。
在被市场验证了“找出异常/伪人”这一核心概念的价值后,玩家开始寻求在这一框架内更具深度和复杂性的体验。玩家的注意焦点从“房间里哪里变了?”,转向了对游戏世界观的探讨、对角色故事与动机的猜测,以及对自己选择的道德后果的思考,即“我能信任什么?”。玩家们试图从碎片化的线索中拼凑出世界与自我的真相,这种对故事和背景的强烈兴趣表明,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从简单的差异识别到复杂的社会模拟的类型进化,“伪人”类游戏可以承载更复杂的互动系统与更深刻的叙事。
直面脆弱
“伪人”恐怖游戏最核心的吸引力,在于其对玩家心理的精准打击,即那种“持续的不安,因为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他们”。玩家能“直观地感到恐惧,但却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游戏的设计目标明确指向让玩家陷入“偏执”与“敏感”。
这种基于偏执的恐怖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直接攻击了玩家最基础的认知功能:模式识别、社会判断和短期记忆。在异常类游戏中,游戏将玩家的大脑训练成一台敏感的“找茬”机器,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警报。而在《寻找伪人》中,玩家的社交直觉和同理心这些基本能力变得不可靠,游戏在玩家心中植入了一种深刻而持久的心理脆弱感。这种源于认知失调的恐惧,远比短暂的突发惊吓更为高级和令人回味。
想象的恐怖
模拟恐怖的低保真美学,在玩家体验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乍看之下,粗糙的画质似乎是沉浸感的障碍,但玩家的反馈却恰恰相反,这种“粗糙”感本身似乎就成为了一种恐怖源。
这背后是深刻的心理学原理。首先,低保真视觉效果利用了“模糊性原则”,即人类大脑有一种天生的倾向,会在不完整或模糊的信息中填充内容与意义。当画面被模糊化时,游戏便将营造恐怖的责任部分地转嫁给了玩家自己的想象力。玩家大脑自行脑补出的怪物与情节,往往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模型与剧本都更可怕。其次,不完美的人类模型极易触发“恐怖谷效应”。当一个形象“足够像人,但又不够像人”时,会引发观众生理上强烈的反感和恐惧。
“伪人”类游戏中被广泛应用的模拟媒介,如老式摄像头、收音机、调频电视等,其本质特征是信号会随着时间和复制次数而衰减、失真,且易受干扰。它是一种天生就“不可靠”的信息载体。这种技术层面的不可靠性,与游戏核心叙事中的不可靠的他者(无法信任他人)和不可靠的理性(无法确定“规则”与真实)形成了完美的互文关系。玩家不仅无法信任门外的访客,甚至无法完全信任自己赖以认识外界的媒介本身。这种多层次的、对感知能力的攻击,共同构建了一种系统性的偏执体验,将游戏的恐怖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

恐怖:文化与时代
“伪人”游戏中为玩家带来的心理恐怖体验并非凭空而来,在笔者看来,恐怖作为一种心理与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人类生理、文化与时代的深层土壤。这一节中,笔者将尝试架高视野,从恐怖这一基本现象来分析恐怖游戏与泛恐怖题材艺术。
作为生理的恐怖
生理恐怖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观的恐怖。当面对直接的人身安全以至于生命威胁时,恐怖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现象自然地、迅速地浮现。面对生理恐惧,人类将激起最原始的“战”或“逃”的快速生理反应。
基于这种原始的恐怖,许多经典的恐怖形式被设计出来:从现实的“鬼屋”,到电影、游戏的“jump scare”、血浆恐怖等。
作为文化的恐怖
相比生理恐怖,作为文化的恐怖无疑更深入人心,也更加持久。笔者在这里想要引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来理解一个经典的恐怖划分方式:中式恐怖(东方/日式恐怖)与西式恐怖。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分别指向了不同的社会愿景与社会生活:一种文化认为社会、世界存在固有的、确定的、和谐的秩序,社会的愿景与目的都应该是靠近或者说恢复那种和谐。这就是“阿波罗式文化”,斯宾格勒用此描述追求形式、结构完美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它与追求社会秩序、天人平衡的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非常贴近的;另一种文化认为矛盾是世界的内在,所以永远追求进步、追求探索与征服,永不满足。这是“浮士德式文化”。其内核与近代以后的西方文化是很接近的。在现实世界中,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现实中的东西方文化中也都存在这两种形态的混合。但将其作为文化的底色来认识,笔者认为是存在可取之处的。
那么,基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核,恐怖的表现形式也不同,或者说能够唤起恐怖的事物与情形有着不同:传统中式恐怖的表现形式通常是“反常”的诡异、原有秩序的失衡:一个怨灵的出现,打破了阴阳两界的平衡;一个熟悉的日常场景,因为某个细节的“反常”而变得诡异。这是阿波罗式文化的受阻; 传统西式恐怖的表现形式通常是探索的反噬与生理恐怖的结合:一群年轻人闯入禁地,必然会唤醒沉睡的杀人魔;科学家进行禁忌实验,最终会创造出失控的怪物;宇航员探索外太空,带回的却是致命的异形。这是浮士德式文化的受阻。
在现代,这两种文化形态逐渐交融,我们也懂科学与辩证,西方人也懂太极与阴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恐怖文学、恐怖影片、恐怖游戏上二者也存在融合之相。如温子仁恐怖电影的火热,“异常”游戏、“伪人”游戏的流行等等。
对于上文所提及的“阿波罗式文化”,笔者其实做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解读。斯宾格勒所强调的“阿波罗式”的原意是和谐与秩序:其中,主要指的是古希腊/罗马的“人与世界”的和谐与秩序,核心是对自身理性与世界秩序的认识,最终指向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与后来的科学;相比之下,东方强调的则是“人与人”的和谐与秩序,核心是对人伦关系与社会秩序的认识,哪怕是强调自然的阴阳与道教,也是以自然喻人,其最终指向一种伦理学、政治哲学与社会学。在这个角度上,笔者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做了一些扩充与延展。
通过这个角度来说,现代西方文化的底色无疑是古希腊/罗马阿波罗式文化与浮士德文化的融合体。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西式恐怖中的一些部分:“不可知”的恐怖(克苏鲁式恐怖)的根源。既然西方阿波罗式文化的秩序根植于一个可知的、理性的宇宙,那么最深层的恐怖就是“认识论的恐怖”——当人类发现宇宙的真相是不可知、非理性、无法认识的,整个文化的安全感就崩溃了。恐怖来自于“世界”的真面目揭示了人是何等渺小和无知。
现在,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文化形态理论框架来对“伪人”游戏的恐怖内核进行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着两类“阿波罗式”文化的受阻:理性的失衡(客观规律的失效与恐怖谷效应)与社会的失序(信任的瓦解与社会结构的崩塌),也可以发现“浮士德式”实践下的威胁:玩家通常不是被动地等待秩序崩坏,而是被赋予了一个主动的“探索者”或“守门人”的角色。你需要主动去观察、去盘问、去分析,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对抗来自外部的、充满敌意的威胁。每一次开门或是不开门的决定,都是一次直面凶险、并承担其后果的浮士德式赌博。这种“探索-对抗-反噬”的循环,又十分契合西式恐怖的逻辑。这也许是“伪人”游戏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搏得共鸣的根源。
作为时代的恐怖
不仅仅是生理恐怖、文化恐怖,基于时代的恐怖也会引起社会与个体的高度共鸣。首先,我们不妨将更视角浓缩一些,聚焦恐怖片这种恐怖形式:恐怖片这一类型,比其他任何电影类型都更能直接地反映、或显示出社会最深层的焦虑。恐怖片并非创造恐惧,而是释放并赋予早已存在的社会紧张情绪的一个具体的形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恐怖艺术为被压抑的、甚至可能是反文明的情感(即社会集体意识中的“本我”)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通过艺术的形式使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变得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流行的恐怖一定与时代的创伤和焦虑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破碎的国家精神与权力思考(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内缩与个人困境(弗兰肯斯坦、德古拉);二战后期的原子能反思与怪物恐惧(哥斯拉);冷战期间的阶级叙事与社会分裂、虚无主义(驱魔人、活死人之夜);冷战末及新时代的道德滑坡与女性困境(月光光心慌慌、猛鬼街);911后的不安全性恐惧与道德困境(电锯惊魂、人皮客栈);现代的种族主义与身份叙事(逃出绝命镇)等等。
在《寻找伪人》中,我们似乎也能窥见到其背后的时代创伤。

信条:选择与意义
这一节中,我们从宏观恐惧理论回归游戏本身,在笔者看来,恐怖是一种形式与框架,而其叙事的内容与核心是作者想要呈现的信条与意义。
《寻找伪人》(No, I'm not a Human)中,我们会遇到超过50位不同的访客,抛开那些不能说话的、无思维逻辑的,他们中绝大多数都通过外表、语言体现着不同的价值信念与生活意义,并据此表现不同的行为。在游玩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伪人并不是一定会杀人,而真人也不都是无害的。这也许是作者对于“伪人”这一概念的一种解构。
那么,扮演屋主的玩家,我们应该相信谁?我们如何进行判断?——是否相信电视台?是否相信收音机?杀掉每一个疑似伪人的人?拒绝任何一个有攻击性的人?无视每一个“神神叨叨”的对话?还是相信“预言”并依此行动?在笔者看来,这已经远不是过去的“伪人”游戏中常见的“找不同、找异常”的流于形式,而是到达了一种新的境界:对自我道德与价值信念的一种内向审视。

《寻找伪人》(No, I'm not a Human)作为自测试阶段就备受关注的“伪人”类游戏,其营造的氛围感与心理恐怖表现十分优秀,并开创性地将信念叙事融入了“伪人”类游戏中。制作组精准地利用了社会文化的弱点,并几乎完美地寓言化了时代的创伤,并最终将一个个关乎道德与信念的难题抛给了屏幕前的你我。毫无疑问,《寻找伪人》是难得的“伪人”类游戏佳作,甚至于指引了该类型游戏的演进方向。
在本篇中,笔者引用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并尝试性地对其框架进行了延展,并基于此进行了对“恐怖”这一心理、社会现象的一般性理论分析,其中多有不足,还望诸位海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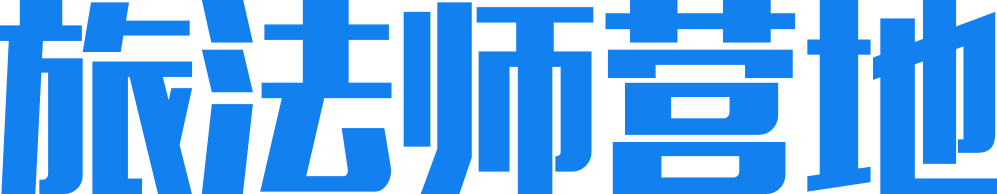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